原创 孟子义、宋茜和徐志胜的向上社交全过程
最近,我重新开始观看《五十公里桃花坞》,并且深深沉浸其中。尽管我在第一季已经看过并且很喜欢这个节目,尤其是它通过对明星们社交行为的观察,巧妙地将社会学理论呈现出来,但第二季以后,节目中的社交观察明显减少,令我兴趣减退。
不过,最近因为宁静在节目中制造的“尴尬9分钟”让我对她的社交焦虑有了新的认知,身边也有几位朋友分享了他们在职场和生活中的社交焦虑和困惑,并问我是否有类似的感受。这让我不禁重新思考社交问题,因此也重新燃起了我对《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兴趣。
我常常担心自己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得到的感触和灵感会被遗忘,所以我决定将这些思考记录下来,和每个在社交中感到焦虑的人说一句:“没关系,别因为这个觉得自己不好,因为每个人都有社交焦虑。只是有的人选择显露出来,而有的人则深深埋藏在心底。”

《五十公里桃花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社交焦虑案例,分别来自宋茜和徐志胜。首先来说说宋茜。这个节目通过将不同年龄段、性格迥异的艺人聚集到一个陌生的社区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展现他们在社交中的不同反应与互动。节目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桃花坞”的理解和看法。例如,宋丹丹认为既然是节目,大家就应该有集体意识,并为观众提供看点,因此她常常表现得有些强迫感。虽然很多人觉得宋丹丹这种行为有点过于强势,但我理解她作为喜剧演员的心情,因为他们往往会把观众的反应视为至关重要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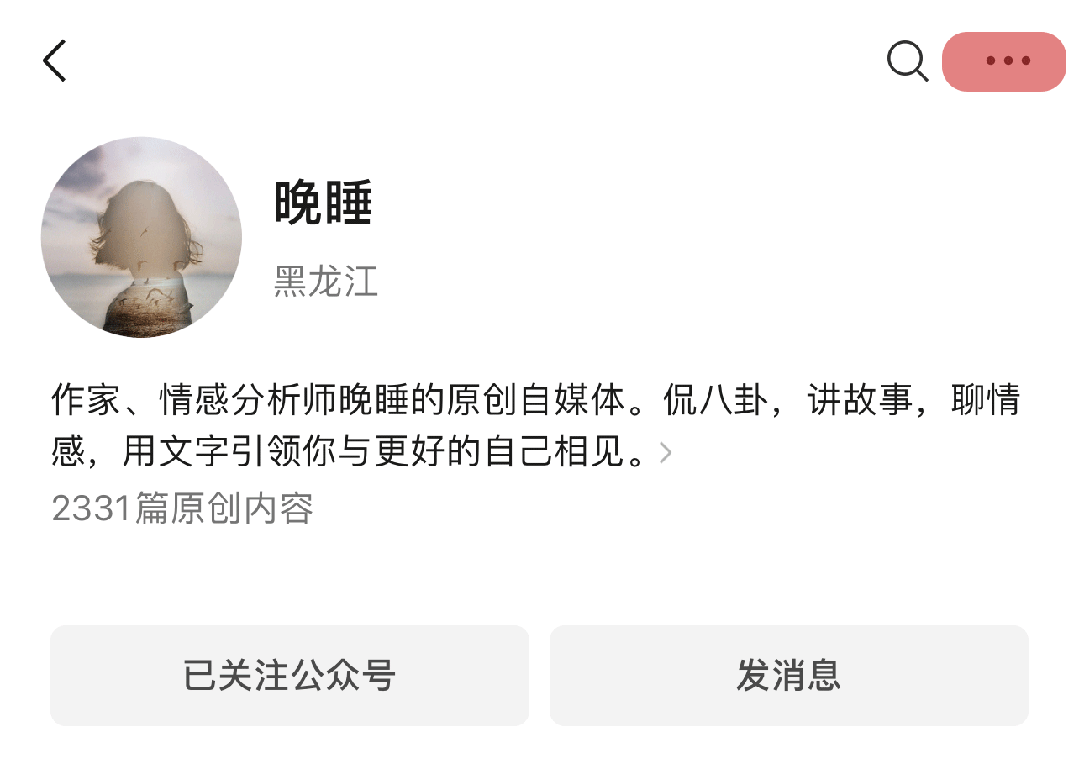
然而,节目中的一些艺人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觉得来到桃花坞就是为了做自己、放松心情。所以桃花坞的社交生态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认同集体意识,愿意在社交中努力融入,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做自己,敢于抵制集体活动,甚至干脆放任自流。
在第三季的广场舞比赛中,节目组要求各个房间以团队为单位进行比赛,但其他两个房间的成员对此并不在意,甚至表示弃权。相反,宋茜是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她为了这次比赛练舞跳得十分认真,甚至要求自己的队员们一起排练。她认为既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最终,她因为自己的过于认真而泪流满面。

当时,我瞬间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哭。其实在桃花坞这个社交场域中,背后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权力较量,每一次社交都伴随着一定的C位之争,只有占据高位的人才能在社交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宋茜作为新进成员,而且性格上不喜欢突出自己,因此在这个社交环境里,她处于一种相对低位的角色。与此同时,那些反对“卷入”集体活动、追求自由个性的人,在社交生态中逐渐成了上位者。
其实,这种不言而喻的“排斥”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压力,它会让其他成员不得不下意识地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趋向那些上位者的行为模式,以便获得认可。因此,我发现大型社交场合中的上位者总是能更容易地感受到满足,而下位者则往往伴随着孤独感。
宋茜在看到其他人轻松应对舞蹈时,自己却认真得几乎过于投入,她感到自己的付出似乎给大家带来了压力。而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她在这场社交中感到自己并没有融入上位者的圈子。人性中有一种天生的趋同欲望,每当进入社交环境时,我们总会渴望被接纳。那些完全没有被社会群体接纳的人,试图自我接纳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这几乎等同于认命。

在《五十公里桃花坞》观看的五季中,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当我们成为社交中的上位者时,我们更容易获得自我接纳的机会,因为这时我们已被社会接纳。孟子义和徐志胜这两位角色的转变尤其显著。孟子义在前三季虽然表现得有趣,但并不属于桃花坞的社交上位者,她更多的是通过钝感力来缓解自己在社交中的孤独感。而到了第四季、第五季,孟子义明显已经成为了桃花坞社交中的上位者,从而找到了真正的放松与自在。
徐志胜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作为喜剧演员,他通过幽默和梗来掩饰自己融入群体的疲惫和孤独。他总是充当那个社交下位者的角色,表现得非常容易亲近,能和任何人开玩笑,实际上这也是他生存于娱乐圈的本事。他的这种自我牺牲,让他在与大海面对面谈心时,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因为他曾经为了融入大家的世界,连系鞋带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这种辛酸,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体会。我们常常在大型社交场合中感到孤独与不安,我自己也曾经有过因为害怕打扰而选择忍耐的时刻。直到多年后,我才学会了如何在社交中自如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包括简单的:“不好意思,我想去趟洗手间”。
我深深认同宋茜的那句:“人啊,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与人相处都很难,与静物相处则比较容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甚至能从风吹过、植物的微动中,感受到一种回应。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张爱玲等高敏感作家的独特体验,实际上在社交场合中感到孤独与焦虑,几乎是每个人共同的命运。

我们能做的,是努力拥有更多选择社交的自由,能够选择那些愿意和自己交往的人。在社交中适度孤独、适当自由,或许才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追求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享受人生的每一份宁静与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