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詹青云和庞颖聊完,我神清气爽

《三块广告牌》
2023年,性别议题依然争议不断。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中,攻击彼此的观点,难以达成理解。
但必须承认的是,正是一次次争论推动着女性主义进入大众的视线,直到它成为不容忽视的部分。
今年6月,在理想家线下沙龙活动中,《思辨力35讲:像辩手一样思考》主讲人庞颖,和《正义与现实:像律师一样思考》主讲人詹青云,与在场的理想家们一起,探讨了现实中作为女性的不同可能性与选择。
就像庞颖说的,“很多时候站在路程中的某一点,容易看走在前面的人不顺眼,看走在后面的人也不顺眼。我们不知道大家都站在什么位置,但希望大家能够以一个比较轻松的角度,比较包容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话题。”
首先,让我们从女性切实的观察和自身的体验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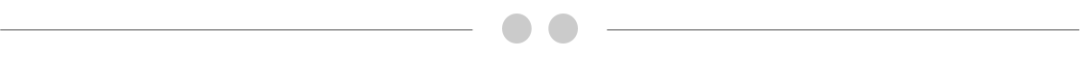
对谈 | 庞颖x詹青云
来源 | 看理想app理想家沙龙
01.
性同意,也是父权制的残留概念
詹青云:我的法律节目结束了后,看理想一直催我整理出书,但我真的很懒,目前处于无限停滞的状态。最近我打算翻译一本书,比写自己的书容易,它的作者是哈佛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亚裔教授。我认为这本书回答了学法律,且对女性视角感兴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说法律没有做到男女一视同仁、男女平等吗?如果翻开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法律,你是很难找到任何歧视证据的。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一波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我的偶像金斯伯格,她们去改良法律所要挑战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
那个时代的法律,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有很多父权的特质。大家可能知道法律的历史,从《罗马法》开始,父权制就是写进法律里的。比如《罗马法》中,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几乎完全被认定为一个家的主人。在这样的法律面前,女人是不被认为有独立于她丈夫之外的人格自主权。
《罗马法》的影响一直绵延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女权运动要挑战法律的不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因为不公实在是太明显地写在法律之中。到了今天,所有现代文明国家一定会在自己的《宪法》里说,法律予以男女平等的保护。
而我在翻译的这本书的作者,Jeannie Suk,就在回答一个问题:当父权制的法律从法律体系上被推翻后,为什么我们仍然觉得不公随处可见?法律为什么仍然辜负了为它牺牲的一代人,以及之后的又一代人?法律还能做什么?

庞颖:能举点具体的例子吗?比如以前女性没有投票权,没有经济自主权,这些比较显性,是否有一些更隐性的例子?
詹青云:传统的《刑法》中是没有“婚内强奸”这个概念的。男女结婚后,丈夫被认为对妻子有绝对的性权力,因此不存在婚内强奸。现代社会是认为有婚内强奸的,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双方都必须获得性同意,才不构成强奸。
但Suk教授说,如果你细想“性同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父权制法律的残留。为什么我们要用性同意和暴力两个概念去定义强奸?为什么会有性同意?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女性觉得她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就是交付了自己的性同意,从此以后进入婚姻,性同意不再是一个问题。今天,性同意的概念更普及了,进入婚姻后也存在性同意,可是我们在讨论强奸这个概念时,仍然以暴力和性同意作为基石。而对暴力的定义,仍然是以“男性在性行为中可容许的暴力”的以上为标准,我们把它定义为违反妇女意愿的暴力,不被法律允许的暴力。
这当然带来了非常多争议。到底什么是暴力,什么是性同意;在不平等的关系下,到底是否存在真正的同意?Suk认为,这些争议都来源于,我们仍然在以“我是否愿意交付我的同意”的视角去理解性行为。
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Suk觉得,性行为是不是一种服从和被服从的状态,是理解这个行为本质的关键。可是法律走到今天,并没有从理解这件事的根源上去寻找新的视角,它仍然是传统的视角,只不过看上去标准做了一些改良。表面上,明显的问题消失了,但根深蒂固的问题依然存在,且更难察觉。
庞颖:所以在法律里,对于婚内强奸,对于性同意的设计,还是依赖于一种传统的男女浪漫关系想象,一个主动和被动的想象。
02.
不是性别对立,是与旧体系的对立
詹青云:那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庞颖:我最近有一个爱好,我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谁说他们家有孩子,无论男生女生,我就会问你们家家务怎么分,能做到对半分吗?
前两天我们公司培训,我旁边坐着一个白男,曾经在美国部队服务过,后来他转行进入了商界。他搬到了华盛顿,在郊区买了一个有草地的房子。现在有了孩子,感觉整个人生变了,你能想象那是一个传统的美式幸福生活。
我就问他,你们家照顾孩子怎么分?他说平时老婆做得多一点,因为他很忙。我又问他,你不是说你老婆是律师吗,律师不是也很忙吗?他整个人支支吾吾,后来说我工作日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周末可以陪孩子之类的。

《信条》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很多女士,我的很多女同事们,能做到家务五五分开,今天晚上如果是我负责,明天早上就是你带孩子上学。我发现,我越往上走,在我身边的女性,家里有一个五五分工的环境,几乎是她们可以在事业上继续努力的前提。
从这里我还得出了另外一个观察,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讲这个问题时,第一是讲五五分工。第二,我们常讲男生愿不愿意做全职家长。你会发现,好像只有两个人里牺牲一个人,这个家才能运行下去。
这个现象在中国、美国都是一样的,因为传统上都是用一个家庭去运营这个社会。我们的养老、育儿,社会上能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家里总有小孩和老人的照料需要被解决,但是解决方案必须是家庭内部有人牺牲自己在外部的选择去干这件事。
但为什么是这个体系呢?是因为千百年来我们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两个人结成一个家庭,家庭里有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解决家庭内部事务。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只在现有体系下尝试男女平等,你想到的是男性也有主内的权利。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想解决养老和育儿的负担,在这个体系里就很难做到。
为什么不能改变这个体系呢?这里举一个或许没那么恰当的例子。以前在黑人还是奴隶的时代,经济支柱是由很便宜的劳动力来支撑的。一旦取消了这个近乎免费的劳动力,社会就不得不进行经济转型,想其他办法去解决。那么如今,像照顾老人小孩这种无偿劳动,大部分由女性来承担,如果不让女性做,也不让男性做,那么该由谁去做呢?
这就涉及到更大的问题。有时候人们讲的性别对立,其实是和旧体系的对立。

詹青云:那你想怎么办呢?
庞颖:现在生育率这么低,社会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了。无论是育儿还是照顾老人,我们都需要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把人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
詹青云:这就是《看不见的女性》那本书里说的,无偿的看护劳动,其实创造了这个社会50%的GDP,如果要为这部分劳动付费的话,付不起,知道吧?
庞颖:对,就是那本书里说的。为什么无偿劳动没有被计入GDP里?因为这些由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没人觉得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不如在社会上赚钱来得辛苦、高级。
此外,当国家不把无偿劳动计入GDP,那么想投资育儿设施、养老设施,就没有明确的金钱数字来衡量,因为以前都是由女性完成的无偿劳动。这导致投入到育儿设备和养老设备里的资金是看不见回报的,所以有的政府就不愿意加大建设。我们要量化劳动的价值,首先涉及到观念的改变,然后涉及到整个体系的改变。
03.
隔离,永远不会带来平等
詹青云:以美国法律举例,美国宪法的理念是这样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所以不应该有任何差异性政策,这个是底线。如果要有差异,就必须给出合适的理由。它的审查标准叫严格审查,比如基于人的国籍和种族而做出差异性的政策,政府必须要给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理由,以及证明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才能通过。
但性别这一项并不是严格审查,法律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确实有先天差异,它不适用于严格审查。所以基于性别制定不同政策,只要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可以了。问题在于,到底该怎么解读合理的理由?这才是推动社会认知不断改变的过程。
金斯波格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判例。美国有一个很精英的军事学院,在历史上只招收男性,而且要通过非常严苛的体能测试才能进入。
有人把军事学院告上了最高法院,理由是他们的规定违反了法律对人的平等保护。对此,学院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历来就是这样,女性和男性在生理上有差异,所以过于严苛的训练和测试对女性是不适合的。
另一方的意见则是,不论适不适合,应该先给她们机会,让那些体能很好的、很有意志力、很有决心的女性去试一试。如果她们不能通过这个测试,不录取她这很正常,但不应该把它当成先天的标准。
而校方接着说,为了维护我们永远是男校的传统,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同等的女校,也是精英的军事学院,只招收女性。

《大法官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作为主笔的大法官,对这件事的经典回应是——这很像种族隔离的年代,有个白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历来都只招收白人,不招收黑人,但是我们为了保持平等,可以建一个同等优秀的学校,只招收黑人。
在种族平权的历史上,后来有一个决定性的诉讼案,即《布朗案》,大法官在该案里表示:隔离永远不平等,“Segregation is never equal。”
同样的道理,把性别置于个人的差异之上,甚至从来不给女性一个机会去试,这种隔离永远都不会是平等的。
但另一方面,这是女权运动当中很重要的分化。有一部分人觉得我们应该淡化这种生理差异,一部分人会觉得要正视不同人群的差异,以及不同差异所带来的困境。
比如面对偷拍这件事,绝大部分被偷拍的受害者是女性,这种恐惧是真实的,如果强行拉到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去比较的方法就比较可疑,因为男人基本上不处于被偷拍的恐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里不能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去看待任何一件事。
我们去评价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代入不同的性别视角,因为不同性别视角所面临的真实困境、真实恐惧,不一定永远是理性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可能导致一个人不那么理性的因素是存在的。
04.
女性要如何找到对女性友好的伴侣?
詹青云: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读波伏娃的书,里面说当女性变成独立自主的人的时候,会遭遇非常大的困境——做一个独立的人和一个女性之间,是有一定取舍的。
一个男生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跟他的男性魅力一致。变成一个更有经济权、决定权的人,能体现他在婚恋市场上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
但是由于我们传统上对女性第二性的想象,女性处在依附和被动的状态。甚至在男女的关系中,女性的性魅力就来源于那种被动和服从。当她追求自己独立的经济权、人格权、决定权的时候,就会降低性魅力。这让很多女性处在困境当中。
而性侵害事件,正是权力的展示。男性有这样的权力,可以让女性无论在乐意、不乐意的情况之下,或者可以不管有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同,去主导关系模式。但是一旦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完全自主权,不受男性控制,会男性的主导地位产生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女性非常主动地展示自己性魅力的时候,男性反而会不喜欢。
很多人会问,一个女性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对女性比较友好的男性伴侣,或者说浪漫对象?我觉得要一分为二来看,如果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只要两个人开心,有一部分隐藏的决策权也可以,这是正常的浪漫。但是一般情况下,是女生更多地隐藏,害怕不这样做就会显得对方没有那么高大、英武,而一段美好的关系,是双方能够彼此欣赏。

《她和她的她》
庞颖:如果两个人能真的把彼此当成平等的人去相处,那么不管这个人哪些地方比你强,哪些地方比你弱,你都能够以比较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
在纪录片《大法官金斯伯格》里,金斯伯格跟她丈夫的爱情还是挺甜蜜,挺令人向往的。那里面有一段这样的内容,金斯伯格的丈夫说,他觉得这个女生非常聪明,所以被她吸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优点和擅长的东西,如果一个男生看女生的时候,是被女生的优点吸引,让他觉得很欣赏,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判点,至少能知道对方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比如金斯伯格的丈夫就不会期待她是一个贤妻良母。
💬
观众提问
01.
创造一个更包容、鼓励大家说出来的环境
观众:现在一些女性会通过写“小作文”,表达自己遭受性侵或者是其他不公的经历。但是有很多人会说这个内容可能是虚假的,要如何应对这样的声音呢?
庞颖: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女性或者是任何权力下位者在网上的呼喊,都确实会有错的、假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只是担心它有一定的虚假可能性,就不允许这种声音出现,社会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这几年的舆论有很大的进步,我记得非常清楚,2017年我在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上了一门课叫做性别心理学,我是在那门课上完成了自己的性别意识的启蒙。但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少有关于性别话题的探讨。近两三年,我们有无数的探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可能很多人的“小作文”,最后并不会得到法律的判决,但它就没有意义吗?我觉得不是。在性侵事件里,除了这类案子本身很难取证,还存在文化的问题,很多人并不敢第一时间去提,甚至事情发生后,周围有很多人会劝受害者息事宁人。在整个社会巨大的禁忌文化下,这件事变得愈发隐秘,愈发难解决。
但通过不断地呼喊,大家会知道现在天平之下谁是强势方,谁是弱势方,弱势方发声,对整个天平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她和她的她》
詹青云:有时候,女孩不得不用“小作文”这种所有人都知道不完美的方式,来伸张自己的权利,是因为她们在正常渠道里错过了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为什么有的女人不得不变成“疯女人”?是因为她们做正常女人的时候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退回来说,时至今日,作为一个个体保护自己的方式,不是等到将来只能诉诸于小作文,而是要第一时间去取证、报案、留下证据,学习更好保护自己的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没有必要为此而羞耻。
有的时候很多人对于控诉唯一的论断,就是“有本事你报案,如果法院判了我就信”之类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迷信也很可怕。法律不是检证真相、裁定真相的地方,法院没有时光机,法院也不能通过一个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法院裁定的事情只有一件,在我们现有法律标准之下,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情发生了。可是这不代表发生或没有发生,这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答案。
而创造一个更包容、鼓励大家说出来的环境,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或者在法律的局限之下,“小作文”仍然有它的价值。
02.
“想想以前比现在更糟糕”
观众:刚才谈到说支持女性主义的女生都感到孤独的话,作为一个支持女性主义的男生,我感到更孤独。我是读新闻传播的,本科的时候研究女性主义,但是我后来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困惑。
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落脚点其实是一个男女都平等的社会,我承认系统性的不平等肯定是存在的。男性也会受制于性别规范,或者在一个经济发展放缓的年代,男性会继续被期待要买房买车等等。
男性在女性主义的框架里也是受益的,但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真的是乌烟瘴气,任何讨论都容易发展成对立。我以前有一些朋友也支持女权,但是经过这几年后,可能会很讨厌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会影响他们在某些事上的判断。我自己也对此感到困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女性主义毕竟是一个理论视角,它很难从理论解释一个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对现实世界的判断。如果把它信奉为一个真理,把理论解释后的世界当成一个真实世界,可能就会发生“女性污蔑一位男性在地铁偷拍”那样的情况。
当然这可能是个案,但我看到这样的事会感到心痛,会感到本来女性的处境就不好,发生这样的事后要行动或者提出诉求,会变得更困难。

《不完美受害人》
庞颖:这个视角最终会对男女都受益,但是在过程中,它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推动女性主义会导致有些人短期受益,有些人短期受害,甚至是长期受害。对既得利益者来说,要他们改变肯定比让受害方改变更难,这是人性,没办法。
理论上肯定希望所有人能一起推动这件事,但是实际情况中不太现实。每个人的节奏,每个人的利益,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现在的舆论场特别差,导致很多对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令人讨厌,甚至把朋友变成了敌人。但我坦白讲,现在的舆论环境下,不只是对女性主义这一件事,讨论任何事都非常危险,非常分化。
理性的人就是少数,你一定会孤独,没办法。舆论环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我希望它会触底反弹。作为我们这群人是很不容易的,不停地发声你就有危险,但是你不发声,舆论场又会被别人占去。所以怎么能既保证安全,又能不断推动事情,可能是大家需要想的。
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大家对朋友的定义或许可以稍微宽一点,哪怕和朋友在立场上有细微的差别。有人觉得要推翻才能重建,有人觉得在既定框架下可以改变,这就是女权主义的不同光谱。对朋友的定义宽一点,才能在本来朋友就不多的环境下推动一些事。
詹青云:以前我在大学学政治的时候,政治学课本的第一页就说,左派永远在内斗不休,而右派总能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很无奈,但客观存在的事情。如果作为自由派,你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内斗不休,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光谱上的不同位置,比起骂比你快或比你慢的人,应该尽可能看到我们最终想要去的地方,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只能说永远不停地提醒自己这件事有多重要,而不要让非常容易团结起来的人轻易利用你的内斗来掌握话语权。

然后刘瑜老师在看理想有一个节目叫《可能性的艺术》,其中有一期说,治疗政治性抑郁最好的方法是,想一想过去比现在还糟糕。
那天我在看地铁偷拍事件相关的信息时,突然看到一个人转发评论说,现在的女的太猖狂了,当年我们随口说谁是公交车、谁是黑木耳,谁敢反抗?
这是我读小学、中学时,男同学之间讲的对女性侮辱性极强的词,没有人反抗,所有女孩只装作听不见。你把那时候的贴吧论坛翻出来,有大量这样的话语,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激烈的表达,大家只能默默承受,装作看不见。
可是今天,我们有强烈的反应,有强烈的反抗,哪怕处于一个混乱的、争执的、内斗不休的状态,但是这种事情已经不能被容忍了,我觉得这就是好事。

